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(全文连载)06
2022-10-28 06:59:17 作者:台湾陈女士 来源: 浏览次数:0 网友评论 0 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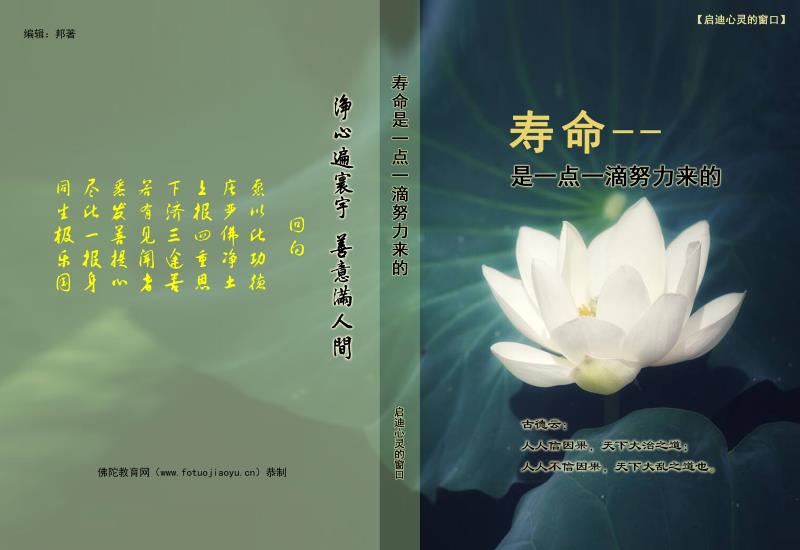
难言之隐
我的事务所刚设立时,地点在台北火车站前面,全体同仁共有廿一人,大半为研究所相关科系毕业,个个品学兼优。
起初十个月,一件案子也没有,几乎寅吃卯粮,支撑得十分艰苦。本来想过不如裁些人以减轻负担,但每个同仁都这般称职尽职,叫我如何开得了口呢?于是,家里能进当铺的值钱物品,可说能当的皆当了。
有一天,我刚出差回来,掌管出纳的会计小姐花容失色地告诉我:“我们抽屉里周转用的公款,全被偷了!”
会计小姐还告诉我,抽屉的锁也被撬开了。她刚请锁匠来修理,并多加了一幅进口的高级锁。
我说:“你再找锁匠来!”我请锁匠把抽屉内外的锁全拆卸掉,什么锁都不要。
会计小姐很不高兴,她问:“为什么把修理好的锁和刚装上去的进口锁都拆了呢?”。
为此,会计小姐终于辞职了,她气愤愤地说我疯了。
第二天,我们周转用的公款又被偷了。我的手头原本很紧,这下更拮据了。我不得已回自己娘家向妈妈开口借了钱。
第三天,这一大笔周转用的公款又被偷了。我好舍不得!几乎哭了出来。
毕竟我已快山穷水尽了,由于无处伸手,只好忍痛把结婚的纪念金表也给当了,
第四天,只丢了一万元,其它一文也没少。第五天,打开抽屉,所有的公款都原封未动,好好的。
我不知为什么,竟然自己失声哭了起来。
这五天,我的同事对我的愚蠢行为几乎都十分不屑,每天都有一些人辞职。试想:跟随这么没有水准的老板,会有什么前途吗?
娘家的妈妈,知道我向她借来的钱是用来摆给窃贼偷的,更是气得好久好久都不理我,不跟我讲话。
家里的另一半和孩子们看我当掉一大堆贵重物品,所有的钱都拿到办公室去摆给窃贼偷,也非常不谅解。
但窃贼总算偷够了,从此再也没有拿过半分钱。我由于周转金大笔失窃,整个事务所元气大损,几乎发不出薪水,所以,又有一批同仁不告而别。
这失窃的事和发不出薪水的事,很快便传到公公耳朵里,便叫我去问话:“你摆钱故意让人家偷的事是真的吗?”
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“你都当了媳妇,也当妈妈了,怎么还这么傻呢?”我说:“我担心对方有难言之隐无法启口,更担心如不及时伸出援手会有生死大灾,所以,每天都尽量多放一点钱来让他偷,希望能暗地帮他忙。”
公公从身上拿出一纸袋的大钞,当面递给我,他说:“你天性如此,讲也没用,这些钱就先拿去济急吧!”
大约过了十多年左右吧,我收到了一张三十五万元的汇票,还附了一封没有落款的短函:
敬启者:
兹奉上办公室当年失窃之三十一万元,另四万元请充当借用十年之利息,还祈查收。谢谢!
又过了十多年左右吧,我因为地中海贫血症发作。被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急救了好几个星期。
突然,有位五十岁上下的陌生太太带了三名儿女来看我:“叫,奶奶!”
她对着我,要小孩子赶快向奶奶问好。
我实在想不起对方到底是谁,也一点都认不出来。
这位陌生太太坐在我的床沿一直静静地淌着泪水,一句话也没说。就这样,她耐心地陪着我,也细心地照顾我,陪到下午六点半才离开。
第二天她又来了,跟第一天完全一样。
第三天一样地,她又来了。
第四天她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可是这一次她开口了。“我能称呼您一声妈妈吗?今天是母亲节!”
她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一张母亲卡。“请问:您到底是谁?”我问。
“我是您办公室里的小姐,我现在与先生住在美国。听同事说您病了,特地全家赶回来看望您,照顾您。请问:十多年前寄还给您的三十五万元收到了吗?”
我恍然大悟,我知道了。我说:“收到了,真谢谢您有这份心。另外多了四万元,我想,等知道寄的人到底是谁时,再当面奉还。”
“不用了,那是利息,不然我内心会很不安的。”她说着说着,禁不住哭了。
“过去的,就让她过去吧!”我安慰她。
“您是我的再生妈妈,是我今生今世的真妈妈,我一定要好好孝顺您,报答您!”
据她断断续续、边哭边述说当年的情节,约略是这样子的:她刚从研究所毕业,便应征进入我的事务所服务,没想到下班途中,被粗野的计程车司机载到山上强暴。她下体全被撕裂,衣裙也被撕裂了。
她刚出社会,没什么积蓄,家境又很苦,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种难言之隐,要找谁求救呢?她在万般无奈下,一天拖过一天,直到下体流脓流血,有生命危险了,才进医院就诊。很不幸地,那位计程车司机罹患有严重的性病,把她给传染了;更不幸的是,她竟然受孕了,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当时,打胎是违法的,合法的妇科诊所是不施行这种违法的手术,一般都找地下密医,但这种诊所几乎全是狮子大开口。为此,她也自杀了好几次没死,可见想死也没那般容易!
她问我:“为什么您要拆掉所有的锁,故意让我偷呢?而且放的钱越放越多?”
我一句也回答不出来,我哭了。真的,我能说什么呢?
一周后,她和先生、孩子们准备回美国,夫妻都已是博士,也都在当地公家学术机构上班,不能请假太久。
她跪了下来,拉着我的双手:“妈,请到美国和我们一起住好吗?我们都很想您,也都很需要您!我有今天,是您赏赐给我的。”
我摇摇头,哭得更大声。
我牵她起来,实在说,我一点也记不起来,她到底是谁。
总算我多了一个好女儿和好女婿,也多了三位外孙,而且都是美国博士,不也苦得很值得吗?
附注一:这件事,您相信也好,不信也好,但为了顾及当事人名节,请勿求证。
附注二:我周转金被窃后,我都低着头进出办公室,我好怕我会认出偷钱的人,更怕偷钱的人看到我的脸会难过。
附注三:我的事务所在全盛之时期,总人数超过两百人,各组独立作业,除重要干部外,我几乎认识不到多少人。
附注四:我因地中海绝症,经常被送到各大医院急救,而前来探望的好友与好心人,各方面结缘的都有。所以,每每有不少人,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对方到底是谁,但我也不敢太过失礼开口问对方:“您到底是谁?”想想,对方可以牢牢记住您,而您竟然可以忘了,这哪对得起人家呢!
血红的婚纱
在我们家,父母亲的命令就是圣旨,做子女的绝对不准不服从、有疑问或反抗。
当时我为了工作上的关系,一个人单独居住在靠近台北县泰山乡附近的小村落,与父母亲甚少来往,即使与外婆家,也几乎忙得抽不出空回去。
有一天一大清早,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说他今天把我给嫁了,要我赶快先自己打扮打扮,大约上午九时左右,便会有部男方新娘礼车到我住的地方来接我,新娘礼服会一起送到。我问:“那我上班要怎么办?”
父亲很生气地回答:“还上什么班,都要嫁人了!”
我又问:“男方是谁?”
父亲听了更加生气地在电话那端大声训斥我:“要你嫁就嫁,难道还得你同意吗?在这世界上,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子女幸福的?你有父母做主,真是多世多劫修来的大福气,你高兴都来不及,还有什么好担心的?”
我看父亲真的生气了,再也不敢吭声,便这样乖乖地接受了。本来,做子女的便不可以让父母亲生气,不能让父母亲稍稍不高兴,更不能顶撞父母亲,可是我内心好想知道:“到底哪位白马王子娶了我?是胖,还是瘦?他为什么要娶我?他是哪个科系?做哪一行的?他到底是谁?”
我的肚子里有一箩筐的问号,当然,也对不可知的未来产生无明的莫大恐惧。我的心一直忐忐忑忑,然而“叫你嫁就嫁”毕竟是父亲的命令,也是“违者杀无赦”的圣旨,我又能怎样?
我陷入一阵阵沉思,坐在梳妆台前暗暗淌着泪水,一脸湿嗒嗒地,我已哭到不能上妆了!
曾几何时,一长排车队的喇叭声、鞭炮声,从木人般的痴呆中唤醒了飘飘渺渺的游魂,我猛然睁开眼睛,啊!我该出门了。
匆匆披上男方送来的婚纱,戴上手套,配上耳环、手链、项链等首饰,我想这些行头应该够了,便闭上眼睛,低垂着头,听任男方来的人把我牵上车子,又是几声爆竹,便出发了。
我静静地,似乎很安祥。可是,我脑海里却波涛汹涌。我真的不知道,我要嫁到哪里,很远吗?
我们的车队,六部排成一条长龙,向中兴大桥方向前进,这是当年由台北县前往台北市的唯一信道。我们沿途边放鞭炮,好一片洋洋喜气。
不久,车子到了中兴桥头,突然,前面一大堆人潮把整条大马路全给堵住了,司机只好把车子给停了下来,走到前面查探究竟。媒婆则一直叫嚷着:“新娘礼车半路不准停车!”但前面已塞得水泄不通,又能奈何!
这时,有两、三个人快步往我们的车子跑过来,一直用手拍打我们的车窗,向我们紧急呼救。
“什么事?”“前面出车祸了,有个小孩子倒在血泊中,有生命危险!”
我低着头,蒙着面纱,披着一身重重的白色结婚礼服,但我能见死不救吗?旁边的男生一点反应也没有,我一急,便猛然把穿着高跟鞋的两脚倏地从五升斗里往上抽,顾不了三七二十一,便下车快步奔往车祸地点。“啊!好可怜的小朋友!”是一位小学生被大车给撞伤了,全身还血流不止。我马上弯下身子,把小朋友抱了起来,婚纱在地上血泊中拖,又湿、又粘、又沉重,我一转身立刻往回跑,上了车,立即请求司机倒车,以最快速度把小朋友送往医院急救。
身旁的男生,一样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等小朋友安顿好了,我又被交通警察传唤去做了一大堆笔录。当天,什么吉日良辰全泡汤了。由于新娘婚纱一穿上身便不能再脱下来,也不能更换,所以,我只好一身血淋淋地前往男方的家。
其实,当小朋友急救清醒时,我自己热昏了的头也随着清醒了。
我知道我惹祸了,我已触犯了本省婚姻习俗的严重禁忌,我是注定要吃回头轿了。可是人命关天,我真能见死不救吗?假若时光可以倒流,可以让我重来,我也会一样不顾自己而全心全力以赴。所以,我深深觉悟,不管我的下场会如何悲惨,这都是我注定无法脱身的劫数,我一定会陷进去。
到了男方,有人打开车门,捧着一盘橘子,接我下车。可是,当我一下车,大家都大声惊叫了起来:“怎么会一身是血?”
“怎么白色婚纱会血迹斑斑,成了血衣?”
我低垂着头呆呆地站着。婚纱的下摆满满地全是血,使花童不敢动手去牵。只见男方的人全往屋内跑,把我丢在外头。他们似乎紧急会商去了。
好久好久,有人大声叫着:“把新娘先牵进去好了,免得围观的人越聚越多,大家不好看!”
我被安置在楼上一处隐密的房间,应该不是洞房吧,我坐在板凳上,冷冷地自己一个人。
媒婆说:“结婚喜宴、拜堂、参见公婆等等都免了!这一身血淋淋的婚纱,还能出去丢人现眼吗?”
夜深人静,我仍冷冷地自己一个人坐着,我越哭越伤心。但我的命运是谁也挽回不了。媒婆说:“等客人全走光了,我们就派车送你回去,我们已决定不要你了!”
我一听,赶快拖住媒婆,跪了下来苦苦哀求,但媒婆一点也无动于衷:“你不是喜欢救人吗?为什么现在不好好救救你自己?你以为穿了白色婚纱,你就是救苦救难的白衣观世音菩萨了吗?不自量力!”
我告诉媒婆,我若被送回去,我就只有自己投河自尽了,媒婆似乎也愣了一下,但没说半句话就出去了。
夜越来越深,但我仍然冷冷地自己一个人坐在板凳上,没有见到新郎,也没有见到半个亲人。
渐渐地,我哭累了,禁不住靠在墙壁上,昏昏沉沉地睡了。在迷糊中,我隐约看到了我们家因为我的死而经济陷入绝境的惨状。我知道,我绝对不能死,如果我一个人死了,我们全家也会活不下去。
一个女人一生只能嫁一次,只能穿一次婚纱,这是我们家世代相传的祖宗家法,而今我已穿过了,我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终于提起最大勇气告诉媒婆:我愿意照他们男方的意思坐回头轿回去,我也愿意归还我父亲所拿走的钱。
很快,靠马路边的窗子似乎开始微微亮了。男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我已不再挣扎了,我愿意沦落舞厅当舞女,或卖身酒廊当酒家女,一切都不在乎,只要能早日还清父母所积欠的大笔债务。
这时,有位男生出现了。他会是主角的新郎吗?他什么话也没说,只轻轻带过:“今天一大早,等天一亮,我们就搬出去外面住,你一身是血,把全家老老少少都给吓坏了,所以非离开这个家不可!”
我点了点头。毕竟嫁鸡随鸡,这是女人天生注定的命运,我还能有意见吗?
就这样,我跟着这位从未谋面的男生,悄悄地走出了这个坐一整天冷板凳的家,没有人与我打招呼,也没有人理睬。
新的家是一个小房间,可以勉强挤两个人。当晚,我们将就地完成夫妻终身大事。我好感激新郎没有拒绝我,而新郎对我这新娘的“救人一至忘我”也一直赞不绝口。他说,我的慈悲,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,实在少见。又说,这么漂亮的心,必有这么漂亮的一生,他有一百分之一百的信心。
我原本以为我已世界末日,没有想到竟然奇迹似地峰回路转,有了这么大的转机,我好谢天谢地!
一年后,第一个女儿降生了。依法要报出生,就得先报结婚户口才行。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,也叫我拿出我的身份证。我突然发觉不对,他的名字怎么跟喜帖上印的完全不一样呢?当年我爸告诉我的,也不是这个名字呀!
他笑了。他说:“妈妈,你真糊涂,你嫁给谁,竟然一点都不清楚!”
我说:“爸爸,我哪有可能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呢?”我只知道三从四德,百依百顺,全心全意守护着这个家,我一个小女子哪能想那么多呢!
他说了:“结婚那天,娶你的是我堂哥。可是,你一身白色婚纱,染得红红的满满是血,可把我堂哥给吓坏了,当然也把我伯父母吓坏了。所以,当晚,大家商量好要立刻把你给退回去。但媒婆说这样你会上吊自杀,只有死路一条。而我也坚决反对他们这般残忍的做法。我一再强调新娘的心地又善良、又漂亮,也反问他们:“难道救人有罪吗?”岂奈,我费尽唇舌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铁石心肠,只好在“救人第一”的大前提下,情急智生,自己勇敢地进了洞房,把这婚姻自己一肩挑了起来。反正,你也不认识新郎,嫁给谁不也都一样吗?否则,像你救了别人的命,反倒自己活不了,因而丢了宝贵生命,这世间还有天理吗?”
我听了,真是又气愤又感激,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?我一连好几天不跟他说半句话,而他也好紧张,一再赔不是,赔了又赔。
两年后,他约我一起去“台大”四字头的癌症病房,探望一位长年卧病不起的病人,好象是同宗的亲戚。我第一眼望去,似乎有点面熟。他介绍给我:“这是我堂哥,我伯父母的独生子。”
回过身来,他又向着一对两眼几乎哭瞎了的老人家:“这是我伯父母。”
我直觉地感到这两位老人家好可怜,就只一个独生子,却得了肝癌,而且已到末期了。
出了病房,我问:“我见过这个人吗?我见过这家人吗?”
他说:“这就是当年娶你的那位真正新郎,而那两位老人家就是当年你拜堂的公公婆婆!”
我说:“我能抽空帮忙这两位老人家照顾这个病人吗?我能否给他们两老当女儿,来奉养他们安度下半辈子?”
他点了点头说:“‘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’,这夫妻缘虽然毁在血红的婚纱里,但总是一日珍贵的情。饮水思源,我支持你的善心与善念。”
我想:这人会是血红的婚纱所克死的吗?我当日真的是一名会令人倒霉的新娘吗?古人不是说,“姻缘天注定,半点不由人”吗?为什么既已娶了我,却又不要我呢?
三十多年来,我们一家大小和和乐乐地过得非常美满幸福,丰衣足食,不愁穿,不愁吃;五名儿女也个个孝顺听话,个个力争上游,一一从国内外一流的研究所毕业。像这样的新娘,我真不知哪里不能娶,又为什么男方当日要那般绝情地逼死我呢?
我们一家大小从未口角,或有任何争吵。我们都很珍惜这份缘,这份福;都彼此以一生一世的努力来维持一家的和平,使我们的家成为人间的一块净土与乐园。
我们夫妻也从未分开过,永远手牵着手,在喜悦中,在平凡、平实、平淡中一天平安地度过。
我们两人都有安定的工作,都有十分宽裕的收入,除了美中不足的地中海贫血症外,这一生应无任何缺憾。可见血红的婚纱所庇荫的应该是无穷无尽的福,怎么会是祸呢!
当日几乎所有的亲友都不看好我这一身是血的新娘,大家都怕坏彩头,会惹来大灾或大祸。但事实证明,几乎置我于死地的世俗迷信,完全错误。当时我先生敢于冒杀身之血光劫来与我结为夫妻,也只不过是因为我一身是血是为了救人一命,像这样慈悲的心,怎会没有福报,反倒惹祸呢?时间是最好的证明,我先生是对的。
现在,我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了,也都可以谈论婚嫁了。儿女们说:“妈,像您这样的女人,有谁能休得了您呢?即使新郎是我们,而您当天一身血淋淋,婚纱又乱七八糟,在我们心目中,您依然是这世间最为漂亮的新娘。因为您有一颗漂亮的心!而您救人所延误的时间,也才是神所应许的真正吉日良辰!”
儿女们的安慰,每每使我热泪盈眶、滴滴嗒嗒,有如永远下不完的苦雨!
问题是,实际迎娶的,没进洞房;而进洞房的,却不是真正迎娶的新郎,我真算嫁了吗?我嫁的是那一位?
附注一:有读者问:“为什么不能退婚回自己的家?”
依本省习俗,女儿出门,便是泼出去的水,再回头会拖垮娘家一辈子倒霉透顶,使娘家兄弟姐妹永远无法抬头出头。至于我的处境比这更惨,因为我是被父母卖出去的。我父母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大型印刷工厂,专门承制月历、报章、杂志。可是时运不济,客户倒了,爸妈也支撑不下去,最后被法院查封拍卖了。爸妈为了救急,曾饥不择食向地下钱庄周转了高利贷的黑心钱。当爸妈一无所有时,便落入黑道手里,而爸妈身边除了我这女儿还值点钱可以卖外,可说早已一筹莫展了。这件婚姻,爸妈总算卖到了一大笔钱,也缓解了爸妈一家大小的苦难,脱离黑道,脱离苦海。我绝对不能被退婚。如果我被退婚,爸妈便要退钱,那爸妈不就又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了吗?当一个人死,一家大小就人人不用死,我这随时会死的地中海绝症患者,为什么不能自我一了百了呢?只是我不懂事,一时冲动救人染红了一身婚纱,几乎害父母再度陷入黑道毒手。唉!穷人家有穷人家的悲哀,这是局外人所无法体会的。(这笔债,我婚后还了十年才还完,真没想到血红的婚纱,代价这般高。)
附注二:这件血迹斑斑的血红婚纱,在我庆祝六十大寿之祭拜典礼中,在全体家人的祝福下,奉献给天地,而当场把它给焚化了。当年,出租的婚纱店坚持不要这件婚纱,而且开价要我赔偿,前后交涉了两、三年都不肯让步,几乎使我整个小家庭的生活费濒临崩溃。其实,当年我的生活已经很紧了,连我大女儿喂牛奶的钱都没有着落,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当一个人可怜的时候,什么事都会很可怜。
附注三:本文由于部分情节涉及个人隐私,于校稿时予以删除,故上下文之连贯,或有不尽通顺之处,或甚至因而与真正之事实略有脱节而无法完全吻合,凡此均非得已,还请宽谅。
愿以此功德,平等施一切,我等与众生,皆同成佛道,阿弥陀佛。

 已有
已有
